個人展區
創作者及1F展區位置
可點擊以上作品名稱跳至該作品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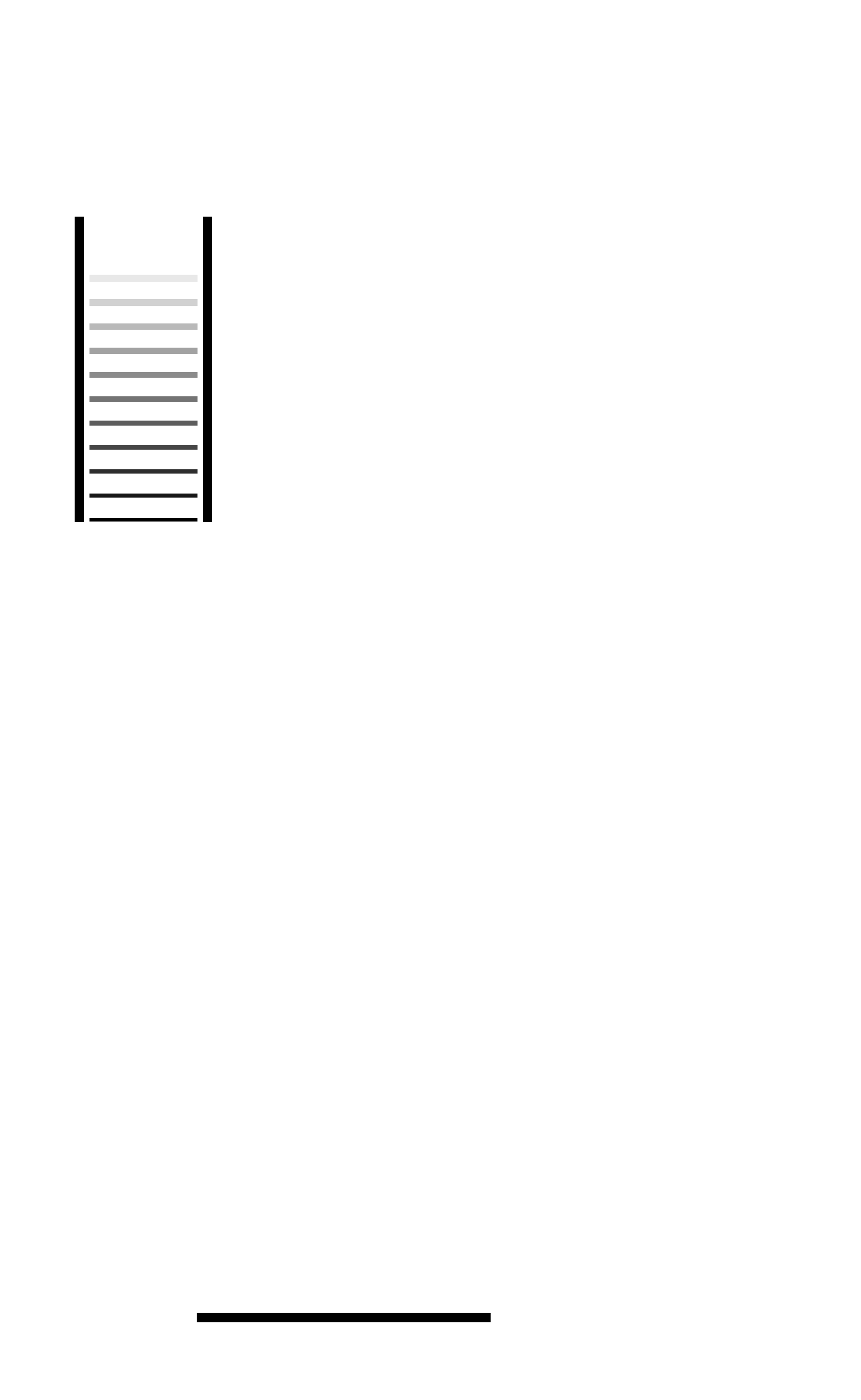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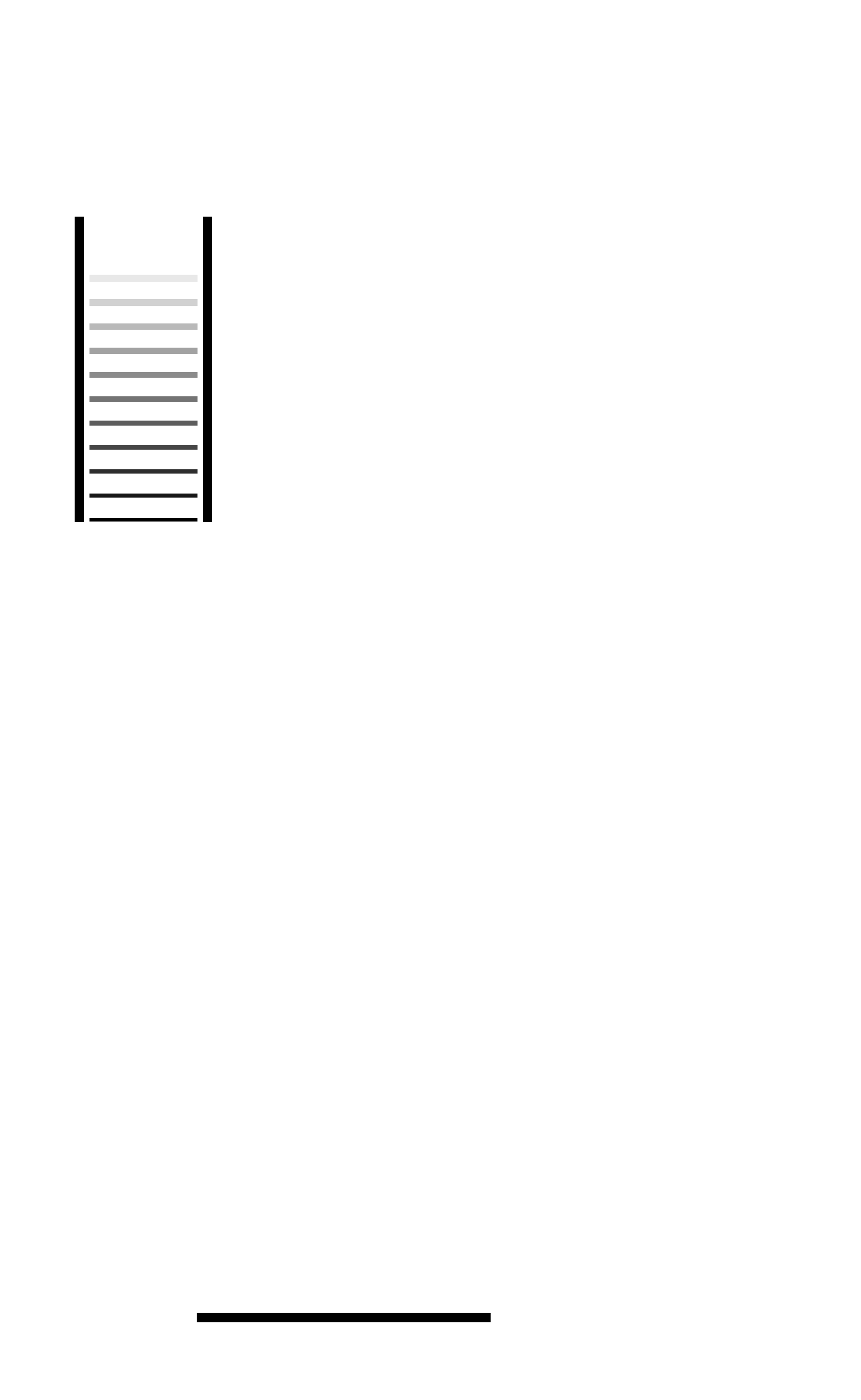

對我來說,鬼魂是藍色的,它們外在形體完備,內在卻異常輕盈。
這件作品我透過塑膠花的實物投影 (photogram),使花成了花的鬼魂,在清透的皮膚和晃蕩的身體之間,我想知道自己和這些鬼魂到底有何區別,人和物、生命和非生命之間,是否並不真正存在界線?

20年末走進了中壢後寮,也不曉得什麼叫作田野,只是看到切分格線就要劃過綿密一如掌紋的地方以及拔除門窗的家屋,才剛打過招呼,就面臨說再見的景況。於是,一直都不是忘記和離開的問題,而是不相關的自己如何留下的回應,在一個就要消失的地方、在一個起始什麼也認不得的地方,疫情隔離的幾個月份以後再相見,綠色工地圍牆描繪的一種未來,已運用拆除及開挖的方法,讓認得的路都不見了,而進入總是遇到了阻擋。
以破壞及過度調色製作的「不完美影像」,表示不是當事人的身份與進入後寮時已無法改變現況的錯時,以感性的創作手法進場,做出情感和記憶能安放的空間,賭在不完美的散落仍然能是聚集的線索,而至今也沒打算忘記後寮的輪廓,為尚未離開而可能的顯像。
人生在世上,不論遭遇多少喜怒哀樂,終究還是得過日子。到台灣後沒地方住,沒法在平原上種稻,只能到山裡種些水果,砍一些木材來湊活。反正就依著河階地形,一層一層往上蓋,依山而居吧。砍到政府不想砍,要把林場改成遊樂區,該怎麼辦?那就將就,把鐵道拾到拾到,以後就開車吧,也不用再與那些卡車爭道,怪可怕的。地震一來,把左鄰右社都震垮了,落個大夥家破人亡,連死人都沒地方埋,又該怎麼辦呢?也不是沒辦法,只要咱們還在,就可以收拾瓦礫,餞行活者的親友,拜別逝去的親友,日子過一天算一天,大家將就一下,眨眼之間,二十來年不也就過去了嗎?

世界總有一個角落是屬於他的。當他的主觀無限膨脹,這世界再也沒有容得下他的地方了。

〈國立臺灣男子監獄〉
2021/5/19因為台灣疫情的加重,政府宣布了三級警戒。隨著疫情延燒、政府管制及媒體渲染,全台風聲鶴唳,如同全民「坐牢」失去了人身自由,而宿舍則成了我的「監獄」
〈占領四人房〉
同寢室友全部返家躲疫情,終於能獨享宿舍房間啦! 宿舍位於大安區天龍國精華地段,捷運站只要五分鐘。格局方正、房間內外的通風極佳,4.85坪面積極適合單身人士,自備家具及每學期9900元租金,即刻入主
〈宿舍野餐〉
晚餐不能內用?擔心出門就中病毒?沒關係,三餐搭配酒精與大自然環境音,在宿舍也能如野餐一般自由

當我在看著一個人的時候,我心思所關注、引起情緒反應的是什麼呢?人總需要他人的愛,才得以明瞭、確認自己值得被愛;人總需要別人的存在,才得以確立自己在世界裡的位置與價值。在大多時候我們的情感、理解與認知都是那段相對的「關係」給我們的,而不是他們本身。
藉由觀看他人,最終得以觀看自己,一方面像圖鑑、紀錄性質的觀看,另一方面引起我與他/她的思考: 我是誰?什麼事物構成我?其他人又是什麼樣子?我們的關係是什麼? 以較長遠的眼光視之,算是我完整我在此時人生階段的其中一步吧。

噩夢般的一年,生命中所有事物都彷彿被加速了凋零的過程,墜落一般朝著死亡奔去。身體、心靈、希望、情緒、誓約、情感、夢想,種種世界上最重要的東西都崩解著,而自己只能如同看著玻璃罐內的實驗體一般,理性而無力的感受著這一切。
萬物自誕生便不停奔向死亡,欲凍結的都化為餘燼,緊握著的只剩下殘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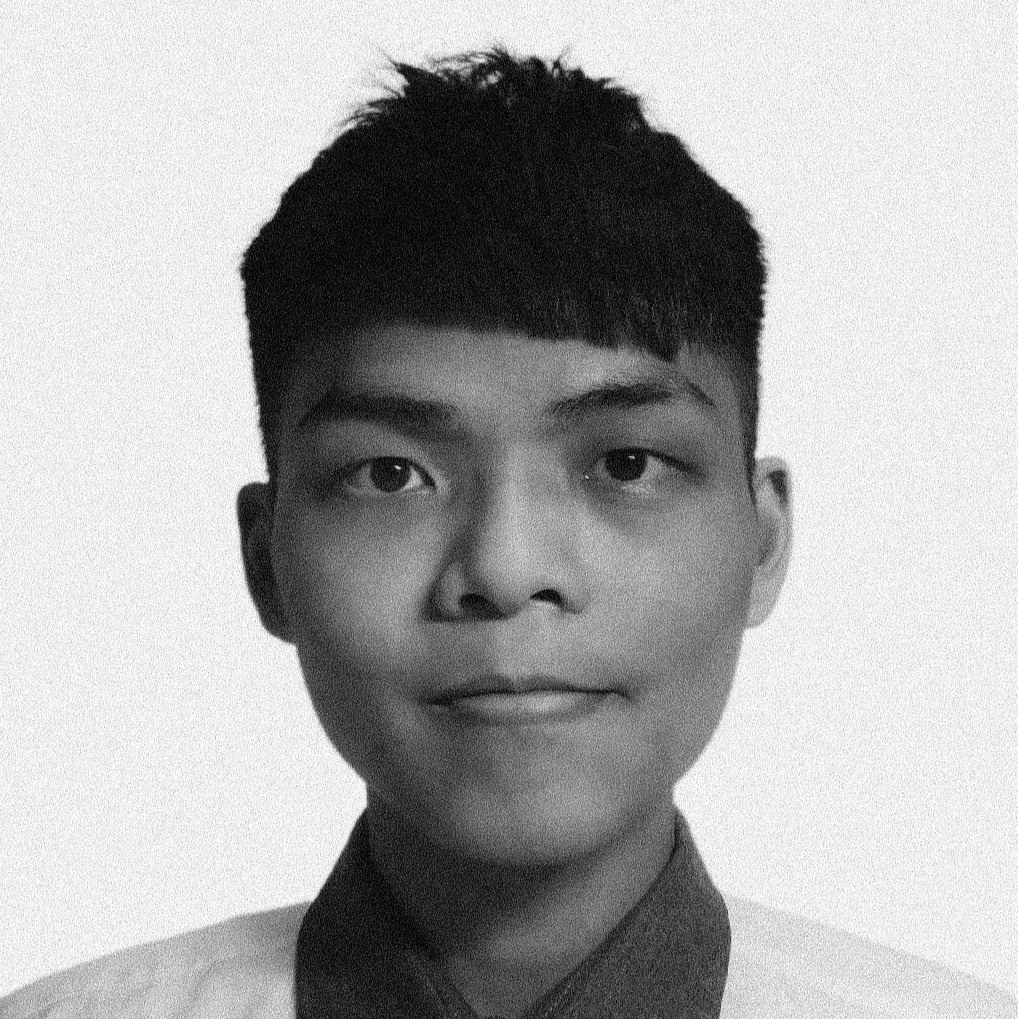
小時候的我們,對周遭的環境有著諸多不滿,當我們面對環境中的「不合理」,就總想著要反抗,無畏他人眼光,與規則衝撞;長大後的我們——遵循著一個制式化的成長過程之後,依然對身處的環境、社會,懷有不滿,我們又做出了什麼樣的選擇?